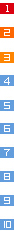新華網(wǎng)北京7月6日電(記者白旭、呂秋平、黃燕、岳瑞芳)八百年后,盧溝橋仿佛一位歷經(jīng)滄桑的老人靜靜地立于永定河上,橋下的河水因干旱已變得很淺,橋上那些被歲月磨損的石獅已被更換。旁邊的新橋代替它承載了交通功能,不遠(yuǎn)處一列高鐵飛馳而過。
橋一端連著宛平城。這個(gè)位于北京西南郊的小城曾經(jīng)是京畿要塞,如今在夏日中安寧得仿佛睡著了,不過城墻上面密布的彈孔卻一直提醒著人們77年前那場(chǎng)戰(zhàn)斗的慘烈。
“這里是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zhēng)開始的地方,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全面抗戰(zhàn)的爆發(fā)地。”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zhēng)紀(jì)念館副館長(zhǎng)李宗遠(yuǎn)說。
苦難的記憶
91歲的楊淑芳老人坐在宛平敬老院的床上,望著外面暑氣蒸騰的院子,就如同1937年7月的那一天。
“那時(shí)候我父親剛剛?cè)ナ啦痪谩!彼@樣開始回憶,“我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上了三年私塾,正放假在家。”她家當(dāng)時(shí)住在長(zhǎng)辛店,距離盧溝橋大約四公里。
一天她突然聽到了密集的槍聲。“最開始我以為是(士兵)打靶,但是不久就有人在外面喊‘來日本人了’。”
今年83歲的周蕊當(dāng)年住在盧溝橋邊,每天和母親打草、收柴。槍炮聲讓她們非常害怕。“我們就躲在炕沿底下。”她說,“當(dāng)時(shí)也沒有表,不知道蹲了多久。”
兩位當(dāng)年的小女孩并不知道,這槍聲一響,就是八年。
關(guān)于那一天,歷史上的記錄是這樣的:7月7日夜,日軍一部在盧溝橋附近借“軍事演習(xí)”之名,向中國駐軍尋釁,并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jìn)入宛平縣城搜查。日方的無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絕。當(dāng)交涉還在進(jìn)行時(shí),日軍即向盧溝橋一帶的中國駐軍發(fā)動(dòng)攻擊,并炮轟宛平縣城。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
宛平敬老院負(fù)責(zé)人陳永利聽到的經(jīng)過是從一位姓崔的老人那里獲得的,崔老曾是二十九軍的一名士兵。
“他告訴我,他們?cè)诒R溝橋打了一天一夜,然后撤到了豐臺(tái),最后到了南苑。”老陳說。
在這個(gè)過程中,佟麟閣和趙登禹兩位將軍相繼殉國,他們的遺物連同布滿彈孔的一段樹干被保存在了宛平城中距離敬老院只有數(shù)百米的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zhēng)紀(jì)念館中。
楊淑芳一家由于和鐵路上有些關(guān)系開始了逃難的生活。他們途經(jīng)河北、河南輾轉(zhuǎn)到了廣西,又乘船到了浙江。“當(dāng)時(shí)難民很多,一路上有的被飛機(jī)炸死了,有的翻船淹死了。”她說。
周蕊就沒有那么幸運(yùn)了。日本士兵在盧溝橋附近駐扎了下來,有一些就住到了她家里。她見到日本兵很害怕,所以一直沒有弄清楚究竟住了多少人。只是有一次她母親大著膽子過去看,見到的是桌上的軍用水壺和掛在墻上的刺刀。
日軍的到來給當(dāng)?shù)匕傩諑砹松钪氐臑?zāi)難。楊淑芳說:“日本人的工廠招工,有的女孩子去了就被糟蹋死了。”為了躲避日本兵,很多年輕女孩藏在教堂里,出門前要用鍋底灰把臉涂黑,而她最小的弟弟做學(xué)徒時(shí)被拿槍的日本兵嚇?biāo)懒恕?/p>
1945年日本投降,飽受戰(zhàn)爭(zhēng)之苦的人們用自己的方式慶祝。適逢楊淑芳第三個(gè)兒子出生不久,全家人像過年一樣買了魚還包了餃子。
歷史的變遷
盧溝橋距北京市中心約15公里,曾被馬可·波羅稱為“世界上最好的、獨(dú)一無二的橋”,以其精美的石刻藝術(shù)聞名于世。“盧溝曉月”是“燕京八景”之一,橋畔一座漢白玉碑亭里,清乾隆帝的御筆印證著它昔日的風(fēng)光。
然而1937年7月7日之后它卻成了國恥與苦難的標(biāo)記,宛平城也變得破敗。周蕊記得,解放初期城門樓都已經(jīng)不見了,城墻也很殘破。
在61歲的李秀蘭的回憶中,當(dāng)時(shí)的盧溝橋畔比較荒涼。她1969年到了一家民用爐廠組裝爐具。“那個(gè)時(shí)候城外都是莊稼地,風(fēng)沙打到臉上很疼,上夜班的時(shí)候沒有路燈,伸手不見五指。”她說。
李秀蘭后來住進(jìn)了單位的宿舍,而住在宣武門的丈夫和兒子看望她要乘坐339路公交車。“當(dāng)時(shí)車就從盧溝橋上面走過。”她說。
事實(shí)上,最早的時(shí)候盧溝橋只有兩路公交車通過——從廣安門到云崗的339路和從宣武門到二七廠的309路。
今年51歲的程炳江就曾經(jīng)在339路車上面當(dāng)了兩年的售票員。“全程大約21到22公里。”他說,“但是當(dāng)時(shí)不堵車,從城里到盧溝橋只要半個(gè)小時(shí)。”
當(dāng)時(shí)乘車的大都是上班的人,因此早晚高峰時(shí)那個(gè)紅皮的老式公交車就被擠得滿滿的。“去盧溝橋參觀的人很少,一年也就幾十人,偶爾有一些外國人。”
每當(dāng)車經(jīng)過盧溝橋,程炳江都要為乘客講解。他記得橋上很多獅子都已經(jīng)遺失了,“還有小孩在數(shù)呢。”
41歲的汪焱就是那些年數(shù)獅子的孩子之一。對(duì)她而言,盧溝橋是童年快樂的記憶。
汪焱從1976年起在橋邊的外婆家住了五年多。“我和小伙伴們常常在橋上數(shù)獅子,每次數(shù)的都不一樣;我們還偷偷到城墻上面摘酸棗吃。”她說。
當(dāng)時(shí)永定河水量豐沛。她曾見過河水漲到橋面的高度,站在橋邊感覺要被滔滔流水吞沒,因此嚇得大哭,被母親抱走了。
1981年,汪焱搬走了。又過了五年,盧溝橋歷史文物修復(fù)委員會(huì)成立,拆除了橋上的柏油路和步道,恢復(fù)了古橋的原貌。盧溝橋走車的歷史結(jié)束了。
永遠(yuǎn)的紀(jì)念
時(shí)間如白駒過隙,轉(zhuǎn)眼間又是三十多年過去。
李秀蘭的廠子后來改為生產(chǎn)洗衣機(jī),其品牌“白菊”一度聞名全國,但最終像不少其他國營企業(yè)一樣沒落了,僅余一個(gè)留守處。
橋頭住的農(nóng)民、老城里的居民以及更遠(yuǎn)的拆遷戶包括程炳江陸續(xù)搬進(jìn)了附近一個(gè)新建的小區(qū),盧溝橋周邊漸漸喧鬧了起來。
宛平城中一個(gè)住過日本兵的牲口棚曾被改成人民公社,后在2004年被建成了宛平敬老院。楊淑芳和周蕊相繼住了進(jìn)來。
建成37年的盧溝新橋由于出現(xiàn)塌陷,于2008年底被拆除,次年2009年5月重建后正式通車。
2012年,京廣高鐵通車,火車從盧溝橋畔的高架橋駛過。盧溝橋作為一百年前的原京廣鐵路的起點(diǎn)見證了這一巨變。
北京地鐵14號(hào)線2013年部分開通,今年6月,16號(hào)線的宛平站也破土動(dòng)工。目前經(jīng)過盧溝橋附近的公交線路至少有九條,很快又要開通夜班車,往返盧溝橋更加便利了。
然而,宛平城卻安靜得如同睡著了。
2009年,曾有報(bào)道稱宛平城中的8000余名居民將集體搬出。雖然搬遷進(jìn)度尚不得知,偶見老居民在樹下對(duì)弈,或帶著小孫兒散步,但城中路上大多時(shí)候行人寥寥。
大部分沿主街的房子租給了外地人來開店,但這些店終因游客稀少關(guān)了門,為此地更添一絲落寞。
人氣最旺的應(yīng)該是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zhēng)紀(jì)念館了。
紀(jì)念館所在地原是被炮彈炸毀的宛平縣衙。經(jīng)各界人士包括原29軍軍長(zhǎng)宋哲元后人的倡議,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建了這個(gè)陳列面積接近一個(gè)足球場(chǎng)的白色建筑。
“建筑是傳統(tǒng)的牌坊式風(fēng)格。”副館長(zhǎng)李宗遠(yuǎn)說,“按照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有功績(jī)是要立碑的,因此這樣的建筑風(fēng)格也是對(duì)先烈的緬懷。”
紀(jì)念館1987年7月7日正式對(duì)外開放,截至目前累計(jì)接待訪客2000萬人次。“我們近些年來每年大概有60到70萬參觀者,而且人數(shù)逐年遞增,特殊年份可達(dá)到100萬。”李宗遠(yuǎn)說。
參觀的人中,不乏抗戰(zhàn)的親歷者,坐著輪椅攜子孫來憑吊。也有日本來的參觀者,一些參加過侵華戰(zhàn)爭(zhēng)的老兵前來懺悔。
“《東史郎日記》的作者曾經(jīng)來過,一位名叫島亞壇的老人把他見到的日軍暴行畫了出來在這里展覽。”李宗遠(yuǎn)說。
不遠(yuǎn)處的盧溝橋也見證了人們對(duì)歷史的反思與悔過。2005年,時(shí)年91歲的日軍老兵本多立太郎在橋的中央雙膝跪下謝罪,而2008年,一些日本婦女在此就日本人對(duì)中國造成的傷害道歉。
“紀(jì)念館和盧溝橋現(xiàn)在展示給世人的,不僅是中國人英勇抗戰(zhàn)的不屈精神,還有人們對(duì)和平的向往。”李宗遠(yuǎn)說,“愿戰(zhàn)爭(zhēng)的悲劇不再重演。” | 

d90d583b-4f93-47ce-8a78-9b81b93ada25.jpg)

0986d48a-161e-448d-99a9-ddba8dd998a8.jpg)

080f94e1-665e-4d68-a6ce-580a1a34a3c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