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9月1日新媒體專電 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一些地方中小學開學同上“抗戰(zhàn)公開課”。在課堂上,教師向學生們講述了不少生動但鮮為人知的故事。
抗日“燈塔”延安還有一所日本農工學校
在延安舉行的抗戰(zhàn)公開課上,夏雷老師向同學們介紹了延安有一座專門招收日本人的學校。同學們好奇地發(fā)問:“延安為什么會有日本人學校?”
1940年百團大戰(zhàn)之后,八路軍俘獲的日軍戰(zhàn)俘開始增多。為教育感化他們,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設立一所改造日本戰(zhàn)俘的學校。考慮到戰(zhàn)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和農民階層,自身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經過討論之后,決定將之定名為“工農學校”。學校于1941年5月15日正式舉辦開學典禮,第一批入學的戰(zhàn)俘有11人。此后,八路軍、新四軍在前方俘獲的部分日軍官兵被陸續(xù)送往延安。
夏雷講道:“這些俘虜如何來處理?如何來解決他們生活方面的問題?是殺?是留?當時的日軍俘虜也惴惴不安。”
雖然八路軍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當時中共對日本工農學校學員按照軍團以上干部待遇給予優(yōu)待,伙食標準每人每月36斤細糧,3斤肉。曾在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日軍戰(zhàn)俘香川孝志在回憶著作中寫道:發(fā)給我們的生活費每月3元,當時八路軍排級干部每月只有兩元。“因此,有的人在星期天就到街上去喝兩盅高粱酒。”
日本工農學校校長由日本共產黨人岡野進擔任,為方便日軍戰(zhàn)俘的生活,中央選派了曾在日本留學的趙安博、李初梨來校任職。除了貫穿全天的學習之外,日本工農學校還建有圖書館、操場和俱樂部,豐富學員的學習生活。在這里接受改造的日軍戰(zhàn)俘香川孝志曾回憶,他們在學校玩撲克、圍棋、象棋,甚至還打起了棒球。
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學校被撤銷,日本工農學校累計改造了約500多名日軍戰(zhàn)俘,先后有100多名學員從事敵后統(tǒng)戰(zhàn)工作,或與八路軍并肩作戰(zhàn),由侵略者轉變?yōu)榉捶ㄎ魉箲?zhàn)士。
延安中學學生楊柳穎聽完課說,自己雖然是土生土長的延安人,但對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歷史了解不多。老師的講述讓她知道,中國共產黨以寬闊的胸襟、正義的力量感化、優(yōu)待日軍俘虜,日本兵因此從侵略者變成反戰(zhàn)斗士,更彰顯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正義和偉大。
是誰打響了抗日“第一槍”?
在沈陽的課堂上,一首曲調凄涼哀怨,充滿國破家亡悲憤的歌曲《松花江上》響起,把在場師生帶回了那段屈辱的歷史。
1931年9月18日22時許,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沈陽柳條湖段,并布置假現(xiàn)場,誣稱是中國軍隊所為,并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中國軍隊駐地。
當時駐扎在北大營的是東北軍620團,該團團長王鐵漢說,日本人進攻北大營時,上面?zhèn)鱽怼安辉S抵抗”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里,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對進入營房的日軍,任何人不準開槍還擊,誰惹事,誰負責”。
于是,一場沒有抵抗的屠殺開始了。據史料記載,日本兵一開始都是用刺刀扎,東北軍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鉆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機關槍掃射而死。
王鐵漢為了帶領兄弟們突圍,冒著違抗軍令的風險,命620團士兵待日軍一走近就開火。
北大營一戰(zhàn),日軍傷亡25人,我軍傷亡失蹤總計483人。“我們手上就幾顆子彈都能打成這樣,如果豁出去打,我們旅有1萬多人,那幾百個鬼子肯定被我們全殲!”王鐵漢說。
“可以說,是王鐵漢率部打響了抗日的‘第一槍’,在之后的抗日戰(zhàn)場上,也能見到他的身影。”在場老師說。
東北育才學校學生葉雨晨說,通過學習我們了解到不抵抗并不是真的無人抵抗。面對侵略者的鐵蹄時,不屈的東北軍民敢于抗爭,敢于擔當,這種愛國精神和“寧可戰(zhàn)到一兵一卒,也要堅守抗戰(zhàn)到底”的抗爭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們。
改變美國政府對中國印象的“八孔窯”
在延安中學的校園內,有一排條石砌成的石窯洞,被師生們叫做“八孔窯”,學生們大多知道這里曾是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駐地,卻對他們在延安的活動情況知之甚少。美軍觀察組是什么?在公開課上,教師夏雷準備的一段視頻資料,讓學生們了解到這段塵封的歷史。
1944年7月22日,一家美軍軍用飛機在延安機場成功降落,從機上走下9名年輕的美國軍人和外交官,他們就是美軍延安觀察組的第一批成員。當時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已經進行到最后階段,為了更有效地協(xié)同作戰(zhàn),美國政府希望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直接接觸,于是在重慶、延安和中緬印戰(zhàn)區(qū)總司令史迪威的三方協(xié)調下,這個代號為迪克西使團的美軍觀察組來到了延安。
從1944年到1947年3月,美軍觀察組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翔實的報告,內容涉及邊區(qū)人民的生活,共產黨軍隊的作戰(zhàn)能力,以及外交政策等,為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決策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資料。
美軍觀察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1944年7月28日發(fā)回的第一份電報中,把延安描述為與重慶完全不同的世界,這里有清新的風氣,欣欣向榮的氛圍;沒有乞丐,沒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澤東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與普通老百姓聊天。
這些來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感受的報告讓美國政府對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紅燈籠也能成為“防空雷達”
在重慶66中舉行的抗戰(zhàn)公開課上,老師播放了一段1941年由美國人拍攝的重慶大轟炸的真實紀錄片《苦干》,學生們對其中高高升起的紅燈籠特別感興趣,這些紅色燈籠就是重慶戰(zhàn)時的空襲警報系統(tǒng)。
當時的中國并沒有掌握防空雷達技術。面對日軍戰(zhàn)機頻繁的轟炸,1937年9月成立的重慶市防空司令部借鑒從周朝開始實施的“烽火臺”體系,配備防空監(jiān)視隊、哨。他們在重慶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廣闊區(qū)域,設立了由26支監(jiān)視隊、132所監(jiān)視哨和1所獨立哨組成的防空情報網。
懸1個紅燈籠,是遠在宜昌的監(jiān)視哨發(fā)現(xiàn)日機,其航向可能是重慶,市民應預先準備或疏散;懸2個紅燈籠,是萬縣(萬州)監(jiān)視哨發(fā)現(xiàn)日機,其航向是重慶,大約敵機1小時內將空襲,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警報解除前不許外出。
西南大學教授潘洵說,紅燈籠成為抗戰(zhàn)時期重慶人的共同記憶,也凝結了中國人的抗戰(zhàn)智慧,有時,人們一天要跑兩三次警報。警報解除,人們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補補,該工作就工作,該讀書就讀書。這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更是一種絕不屈服的意志。
聽了“紅燈籠空襲警報”的故事,學生們無不感慨抗日軍民的智慧和樂觀精神。重慶66中學生鄭劍鋒說,本以為頭頂轟炸,那時候的重慶人應該每天生活在驚恐中,但他們卻能將跑警報當成一種正常的生活去規(guī)劃,其中凝聚了中華民族絕不屈服的斗爭意志。(記者:烏夢達、陳國洲、陳晨、王瑩、凌軍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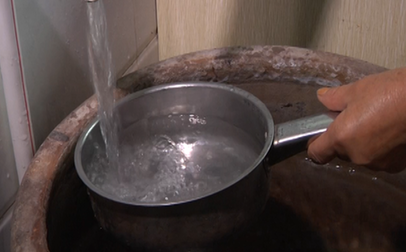




6a021623-d855-40a7-9bf8-08aaf5b66ab0.jpg)
a5de7127-e69e-478c-81e7-3e61224028e2.jpg)


6d31388c-2019-4d9d-adcf-8fd48284b2e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