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是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這一論斷極其深刻,是對法西斯主義的鞭撻、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鞭撻、對所有黑暗勢力和反動勢力的鞭撻,代表了正義的聲音、歷史的聲音,代表了對非正義戰爭的唾棄、對和平的期待和堅持。
在那場正義和邪惡、光明和黑暗、進步和反動的大決戰中,中華民族付出了慘重的犧牲,也經受了脫胎換骨的錘煉。在日本軍國主義的瘋狂侵略面前,中華民族的主體沒有被敵人的殘虐、狂暴、屠殺所嚇倒,沒有屈膝投降,而是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抵抗、堅持正義戰爭,堅持以弱勝強、積小勝為大勝,用持久戰理論指導戰爭的開展,以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為中流砥柱,終于取得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何等艱苦卓絕、何等浴血奮戰,這些都需要長篇巨制的史書詳加記述。習近平同志在回顧中國抗戰“鑄就了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指出中國抗戰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為東方主戰場的歷史性貢獻的同時,強調“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戰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懸在人類頭上。我們要以史為鑒,堅定維護和平的決心”。這就告訴世人,戰爭的危險今天仍然存在,反對戰爭、維護和平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任務。新形勢下,中國歷史學界應下大力氣推進抗日戰爭史研究,反映中華民族在抗日戰爭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歷史,闡明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是如何反對戰爭、爭取并維護和平的。
我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基本狀況
抗日戰爭史基本上屬于中國近代史學科。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近代史研究沒有得到社會和學術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近代史迅速發展成為一門新興學科。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點在晚清歷史,1919年以后的歷史還沒有真正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改革開放以后,學術界視野大開,1919年后的歷史包括中共黨史、國民黨史、民國史和抗戰史研究逐漸提上學術界的研究日程。無論從中共黨史角度,還是從民國史、國民黨史角度,都不能回避抗日戰爭歷史。1982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軍事科學院開始討論與部署抗日戰爭研究課題,提出了撰寫《中國抗日戰爭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任務。
1991年,在胡喬木的關心和推動下,我國成立了以劉大年為會長的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創辦了學會刊物《抗日戰爭研究》,召開了九一八事變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此后,一系列有關抗日戰爭史的學術會議得以舉辦,大量研究抗日戰爭史的論文涌現出來,許多抗日戰爭史料包括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史料公開出版。在此前后,一批抗日戰爭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學術著作先后問世,代表性的著作有軍事科學院的《中國抗日戰爭史》三卷、劉大年主編的《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何理撰著的《抗日戰爭史》以及軍事科學院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朱貴生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等。這些著作正確處理了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系、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與中華民族反侵略的基本格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角色、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關系等問題。與此同時,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學術界也進行了很多討論。比如,關于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究竟哪一個是主戰場,討論中有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從抗日戰爭全過程看,抗戰初期正面戰場是主戰場,從抗戰中期到抗戰后期,主戰場發生了轉化,敵后戰場逐漸成為主戰場。關于抗日戰爭領導權問題,有人認為是共產黨領導的,有人認為是國民黨領導的,有人認為是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也有人認為是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學術上的探討很熱烈。
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劉大年在他主編的《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一書及其他學術論文中,對抗日戰爭史作了理論性概括:要認識抗日戰爭時期歷史的特別復雜性。抗日戰爭首先是民族戰爭,同時也是人民戰爭;其間交叉著錯綜復雜的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階級矛盾;抗日戰爭既是一場民族解放戰爭,又是一場與國內民主革命相結合、相伴隨的戰爭;既有正面戰場,又有敵后戰場;既有國民黨對正面戰場的領導,又有共產黨對敵后戰場的領導。只有依據歷史事實,看到抗日戰爭歷史的復雜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有可能把抗日戰爭史研究中認識不夠深刻的地方進一步弄清楚。劉大年對抗日戰爭史提出了自己的系統認識,這些認識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要點:中國抗日戰爭是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各階級、各民族人民團結起來進行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兩個戰場的存在是決定抗日戰爭面貌和結局的關鍵;在抗日戰爭中,國民黨、共產黨兩個領導中心并存;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根本轉變,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取得對外戰爭的全局勝利。這些認識是很有價值的。
近10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又取得了新進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項目《中國抗日戰爭史》、步平等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全史》等著作出版,研究性的學術論文也很多。其中,《中國抗日戰爭史》著眼于14年抗戰,敘述6年局部抗戰和8年全面抗戰的歷史進程,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用,反映了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壯麗史詩,對抗日戰爭史研究中一些重點難點問題作了新的探討。這本書的貢獻是提出了14年抗戰的概念,強調了中國抗日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強調14年抗戰是有重要意義的,有利于把日本對華侵略聯系起來考察,說明隨著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侵略中國,中國的抗戰就開始了,局部抗戰也是抗戰。當然也應認識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中國抗戰的形勢是完全不一樣的,或者說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在哪里?就在1937年七七事變后的全面抗戰,是在國共兩黨取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識后在國家層面形成的抗戰,是中華民族動員起來的全民族的抗戰,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做戰略配合的抗戰。這種抗戰形態在七七事變前是沒有的。
歐美學者對中國抗日戰爭史的研究
歐美學者在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方面也發表了許多論文,出版了不少專著。許多學者研究中共抗日根據地,對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壯大頗感興趣。也有學者研究國民黨政府,研究正面戰場,研究日本侵華以及日本在華暴行等。蘇聯和俄羅斯學者較多研究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的關系,強調蘇聯對華援助。總體而言,歐美學者對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評價不高,或者基本不涉及。有的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戰場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地位是邊緣的,中國戰場不過是邊緣戰場。有短視的歐美學者甚至完全看不到中國戰場的作用,在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時居然對中國戰場只字不提。
歐美學者對中國戰場的忽視,最典型的表現是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起點或爆發點的認定上。歐美學者、日本學者一般認為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有的學者則把1941年12月7日日本轟炸珍珠港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點。總之,中國抗日戰場不在這些學者的視野之內,是邊緣的甚至可有可無的。這些認識完全不符合歷史實際,是極不公正的,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表現。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復雜,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歐洲中心主義在歐洲歷史學者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不重視中國抗日戰場的作用;二是二戰后出現的冷戰使歐美把中國視為敵對的一方,改變了戰時對中國戰場重要作用的認識;三是二戰時和二戰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是一個弱國,經濟不發達,學術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不大,我們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國際學者的重視。其實,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行過程中,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都對中國抗日戰場有過很高評價。
近年來,由于中國國力逐漸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世界的眼光開始轉向中國,一些歐美歷史學家開始重新審視中國抗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作用。2013年出版的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的著作《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一書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們對‘二戰’中有所貢獻的盟軍的認識,有著巨大的偏差……中國依然是被遺忘的盟友,它的貢獻隨著親歷者的離世而漸漸被人遺忘”“1937—1945年,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東亞地區唯一堅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兩大政黨”“如果沒有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國早在1938年就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那將給日本控制整個亞洲大陸提供有利條件,加速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擴張。一個屈服的中國,也更有利于日本入侵英屬印度”。作者還說:“中國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參與那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尊嚴和生存,還為了所有同盟國的勝利。”這個評價是較為公允的,大體上體現了中國抗日戰場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地位和作用。今年4月法國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了巴黎第一大學著名抵抗運動史專家阿利亞·阿格蘭和著名國際關系史專家羅伯特·弗蘭克主編的專著《1937—1947戰爭——世界》。該書聚集了法、德、意、加、奧等國50多位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學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關注到亞洲,把1937年中國大規模抗擊日本入侵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點,用較大篇幅描述了日本侵略中國以及南京大屠殺等戰爭罪行。該書從全球視野解讀二戰,表達了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其觀點在此前的歐美學者中是不易見到的。今年5月,在俄羅斯科學院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蘇聯、中國在二戰戰勝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中的作用”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代所長盧佳寧在他的學術報告《還原事實真相:1931—1945年間的蘇聯和中國》中認為,中、蘇兩國是擊敗日本法西斯的中堅力量。5月17日,俄羅斯政論家尤里·塔夫羅夫斯基在《獨立報》發表文章《不應遺忘“二戰的另一半”:中國抗戰》。文章首先提出二戰的爆發時間問題,主張應該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二戰的起點,強調中國在二戰中的主體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日本軍國主義、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瘋狂侵略面前,歐洲和亞洲許多國家投降了,法國這樣的歐洲強國只抵抗6周就宣布投降了。中國作為當時世界上飽受欺凌、尚未工業化的落后大國把抵抗侵略的斗爭堅持到了最后,給予世界反法西斯國家重大支援。中國戰場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東方主戰場的貢獻是不可替代的,過低評價中國戰場這個東方主戰場的作用是違反歷史公平原則的,是不科學的。在國際視野下觀察中國抗日戰爭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上出現了兩個戰爭策源地、兩個戰爭爆發點。只有確立了這個認識,才能看到中國戰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略地位和中國人民對戰勝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所作出的重大犧牲與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只有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性、全局性、復雜性的認識和分析中,才能清晰地看出中國抗日戰爭的地位和作用。
推進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建議
習近平同志指出:“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地位和歷史意義相比,同這場戰爭對中華民族和世界的影響相比,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他強調,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必須堅持正確歷史觀、加強規劃和力量整合、加強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強輿論宣傳工作,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著力研究和深入闡釋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意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等重大問題。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對中國學術界特別是歷史學界提出了明確要求,是大力推進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指針和動力。我國歷史學界特別是近代史學界要認真領會講話精神,切實加強、大力推進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究。
一是加強領導,協調全國科研系統、高校、黨史部門和民間力量,協調海峽兩岸的力量,制定抗日戰爭研究科研規劃,提出工作目標,給予經費支持,分工合作、扎扎實實進行嚴謹的學術研究工作,撰寫出版一系列體現科學歷史觀的學術著作。
二是廣泛、深入、全面搜集抗日戰爭史料,包括從相關國家公私檔案館、圖書館搜集涉及中國抗戰以及中國國際關系的檔案、日記、書信、公私文書、照片以及影視作品和各種專門著作,分門別類編輯相關專題的文獻史料,切實打好研究基礎,尊重歷史,用歷史事實說話,使研究著作建立在可靠可信的史料基礎上,成為科學的歷史學著作。
三是切實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國家和地方各級各類檔案館努力為抗日戰爭研究者搜集史料提供最大方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立抗戰史料文獻中心,建立互聯網數據庫,方便學者研究。
四是在涉及抗日戰爭史的一些關鍵問題上開展深入研究,如:日本侵華史、日本戰爭策源地研究;抗戰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史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正面戰場、敵后戰場的戰略配合作用研究;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的空前大覺醒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人心向背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化戰線及文化思想的轉變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際關系特別是與同盟國的關系研究;等等。所有這些研究項目都應建立在大量利用、分析史料的基礎上,產生的史學著作應經得起質疑,具有長久生命力。
五是積極建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國際網絡,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加強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國際學術研討,努力擴大中國學者研究抗日戰爭的國際話語權,爭取產生國際學者共同參與的大部頭中國抗日戰爭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著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
《 人民日報 》( 2015年09月17日 07 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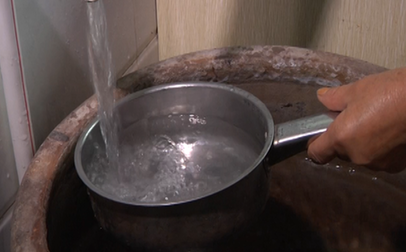

6a021623-d855-40a7-9bf8-08aaf5b66ab0.jpg)
a5de7127-e69e-478c-81e7-3e61224028e2.jpg)


6d31388c-2019-4d9d-adcf-8fd48284b2e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