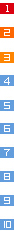近日,一名網絡主播因在直播平臺播出色情內容,被深圳警方以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刑事拘留。網絡直播平臺的火爆、主播的走紅、頻繁發生的直播負面事件,由此引發對相關法律問題的深思:直播色情內容是否構成犯罪?直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如何凈化直播環境?
火爆背后亂象叢生
2016年,被稱為“中國網絡直播元年”。只要一部智能手機和一個注冊賬號,人人都能對著鏡頭當“主播”。
直播到底有多“火”?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2016年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6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達3.25億,占網民總體的45.8%。據艾瑞咨詢今年4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在線直播平臺數量接近200家,其中網絡直播的市場規模約為90億元。方正證券預計,2016年直播市場規模達到150億元,2020年將達到600億元。
網絡直播火爆的背后,也曝出種種亂象。為推高流量、吸引粉絲,主播花樣百出,有的衣著暴露、言語挑逗,更有甚者為炒作不惜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線:今年1月10日晚,某直播平臺出現“直播造娃娃”事件,引起輿論嘩然;3月,某直播平臺一位女主播在直播中突然背對鏡頭,彎腰露出隱私部位……各種惡劣行為在直播平臺時有出現,帶來極為負面的影響。
近日,一“主播”更是因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被深圳警方刑事拘留。近期,深圳市公安局網警支隊開展網絡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8月18日,網警支隊聯合治安巡警支隊、南山公安分局根據深圳市某直播平臺舉報線索,在南山區一出租屋內抓獲涉嫌在網絡直播平臺傳播淫穢物品(淫穢表演)的嫌疑人龍某(女),現場查獲涉嫌用于網絡直播的器材i鄄Pad1部、iPhone6手機1部,情趣內衣一批。
經現場審查,龍某承認其自今年7月以來,通過多個網絡直播平臺等軟件,為他人提供淫穢表演直播,并通過觀看者贈送虛擬禮物的方式非法獲利近2萬元人民幣。目前,龍某因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已被刑事拘留。
直播色情內容算不算傳播淫穢物品
“上述案例中,主播利用網絡直播平臺的運營模式,以牟利為目的,為他人提供淫穢表演直播,以觀看者贈送虛擬禮物的方式非法獲利近2萬元人民幣的行為,觸犯了刑法第363條,符合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的構成要件,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刑法學研究所所長趙天紅副教授告訴本報記者。
趙天紅進一步解釋說,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是指以牟利為目的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侵犯了國家對文化出版物品的管理秩序和社會的公序良俗,主觀上為直接故意,且以牟利為目的。行為人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可以表現為:通過播放、陳列、在互聯網上建立淫穢網站、網頁等方式使淫穢物品讓不特定或者多數人感知以及通過出借、贈送等方式散布、流傳淫穢物品的行為。
根據兩高于2004年聯合發布的《關于辦理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聲訊臺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之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利用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和利用聊天室、論壇、即時通信軟件、電子郵件等方式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均可以認定為本罪中的“傳播淫穢物品”的行為。
什么是“淫穢物品”?刑法第367條給出了答案,即“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淫穢性的書刊、影片、錄像帶、錄音帶、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對于“其他淫穢物品”的范圍,趙天紅說,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包括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淫穢性的視頻文件、音頻文件、電子刊物、圖片、文章、短信息等互聯網、移動通訊終端電子信息和聲訊臺語音信息。
“因此,深圳女主播以牟利為目的傳播淫穢物品,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如果沒有牟利的目的,則其行為可能構成傳播淫穢物品罪。”趙天紅告訴記者。
湖南師范大學瀟湘學者邱興隆教授則認為,盡管在一些網絡直播過程中,直播者所做的動作、語音聊天中的話語具有淫穢的內容,但是,人體動作與語音在不通過錄像、截圖或錄音等固定的情況下,不可能物化為特定的有形的載體,因而不構成淫穢物品。一旦把行為人的身體或動作理解為淫穢物品,那么,行為人便既構成犯罪的主體又構成犯罪的對象,因而勢必混淆犯罪主體與犯罪對象之間的界限。說得嚴重些,是把人當成了物。因此,即使是包含裸體、淫穢動作與淫穢語言的網絡直播行為,雖然傳播了淫穢的場景,但沒有傳播淫穢物品,因而不應被認定為傳播淫穢物品罪。
“但是,如果主播在直播的過程中夾雜有淫穢的動作,而非單純地展示裸體與聊天,便完全可以成立淫穢表演,直播淫穢表演活動的組織者完全可能構成刑法上的組織淫穢表演罪。”邱興隆說。
法律邊界在哪里
接受采訪的專家均指出,網絡直播的內容必須符合我國相關的法律法規,否則,將可能受到法律追究。
哪些能播,哪些不能播?趙天紅分析,總體來說,違反法律法規的直播內容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直播的內容涉及煽動國家分裂、煽動破壞法律實施等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方面的內容;二是直播與淫穢物品和淫穢表演相關的內容;三是直播與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相關或者與邪教相關的內容;四是直播明顯可以認定為是傳授犯罪方法的內容,即直播向他人傳授的某項“技能”為犯罪方法;第五,直播其他違反法律法規內容的行為。
趙天紅還介紹,直播和網絡密不可分,刑法修正案(九)對于非法利用信息網絡行為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行為分別規定了相應的刑事責任,“這也應該引起從事直播行業相關主體的警醒和重視。”
“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即設立用于實施詐騙、傳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銷售違禁物品、管制物品等違法犯罪活動的網站、通訊群組;發布有關制作或者銷售毒品、槍支、淫穢物品等違禁物品、管制物品或者其他違法犯罪信息;為實施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發布信息的行為,情節嚴重的,可能構成非法利用信息網絡罪。“另外,對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行為,可能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趙天紅說。
此外,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副教授吳沈括表示,如果對涉“黃”、涉“低俗”等相關信息不作為,相關平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根據《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網絡出版服務管理規定》的規定,平臺對于色情淫穢等非法信息負有“停止傳輸,及時報告,保留證據”等作為義務。在符合刑法規定的情形下,有可能成立不作為型犯罪,“在刑法層面,往往會涉及相關平臺的不作為刑事責任。”吳沈括說。
如何遏制網絡直播亂象
如何遏制網絡直播亂象?有無必要單獨立法?是否應該加大刑事追究力度?受訪專家表達了各自的觀點。
“線上的行為,平臺提供者應當制定清晰的規則以處理糾紛。線下的行為,則交由各相關部門規范執法。”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陳一天表示,現行刑法、民法、合同法以及網絡安全與文化傳播的相關法律法規足以滿足此類行為的法律需求。“就目前而言,政府部門需要加大執法力度,但不需要針對一種行為制定法律法規。”
邱興隆則認為,直播平臺作為連接網絡主播與公眾的傳播媒介,理應肩負起其應有的社會責任,對所有經由自身向社會傳播的內容進行嚴格的審核與把關。其縱容涉黃涉暴內容的傳播不僅擊穿社會道德底線,更有可能違反相關法律。只有從源頭避免網絡空間受到污染,才能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
“刑法作為一種終極規范,其對社會關系的調整,是以對公民最重要的權利的剝奪為代價的。遏制網絡直播亂象的最有效途徑不是將其犯罪化,而是完善網絡監控與管理措施,加強對網絡直播平臺的管理,要讓違規者看到高昂的違法成本,起到足夠的警示作用。”邱興隆補充說。
趙天紅也認為,刑法自有其謙抑性和終極性,法治之運用與治水相通,在疏不在堵。“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線,在刑法介入規制之前應當重視對網絡直播平臺的監管要求,即首先要確保網絡直播平臺遵守行業自律規范,嚴禁組織、參與實施色情直播或傳播淫穢物品等行為;其次要求網絡直播平臺對主播進行嚴格審查、對其直播行為和內容進行嚴格把關;在政府和文化產業層面上,政府管理部門也應加強對網絡直播的監管,同時,要對網絡文化進行宏觀規范和引導,對網絡直播的受眾進行正確的價值觀引導,促進網絡文化的健康發展。”趙天紅說。(賈陽) | 


ecac1b87-0584-4e51-8164-d6c970c10ddf.jpg)

b16dd201-f29a-41ca-b075-22742c272955.jpg)
3cee39e0-12d7-4dc1-ba9f-2f9ae23cecea.jpg)
9796265c-e0ba-4831-97c9-54358d2b9a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