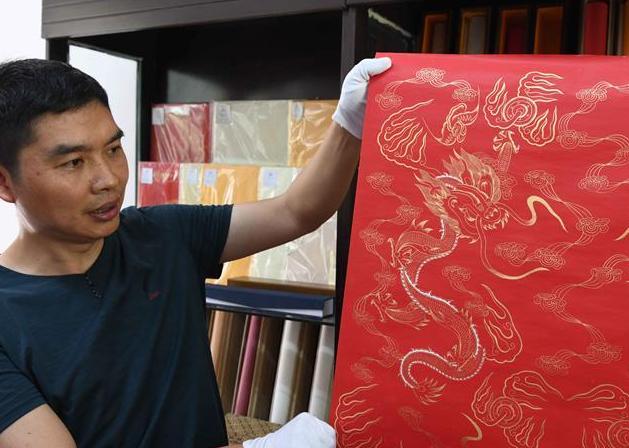|
這是張富清年輕時的照片(3月30日攝)。新華社記者程敏 攝 張富清一年四季幾乎都戴著帽子,不是因為怕冷,而是因為頭部創傷留下后遺癥,變天就痛。 左手拇指關節下,一塊骨頭不同尋常地外凸。原因是負傷后包扎潦草、骨頭變形,回不去了。 多次出生入死,張富清在最慘烈的永豐戰役中幸運地活了下來。 “永豐戰役帶突擊組,夜間上城,奪取敵人碉堡兩個,繳機槍兩挺,打退敵人數次反撲,堅持到天明。我軍進城消滅了敵人。” 這是張富清的立功證書上對永豐戰役的記載。1948年11月,發生在陜西蒲城的這場拼殺,是配合淮海戰役的一次重要戰役。 “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隊總攻就會受阻,解放全中國就會受到影響。”入夜時分,上級指揮員的動員,讓張富清下定了決心。 張富清所在的連是突擊連。他主動請纓,帶領另外兩名戰士組成突擊小組,背上炸藥包和手榴彈,凌晨摸向敵軍碉堡。 一路匍匐,張富清率先攀上城墻,又第一個向著碉堡附近的空地跳下。四米多高的城墻,三四十公斤的負重,張富清腦海里閃過一個念頭:跳下去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就犧牲了,犧牲也是光榮的,是為黨為人民犧牲的。 落地還沒站穩,敵人圍上來了,他端起沖鋒槍一陣掃射,一下子打倒七八個。突然,他感覺自己的頭被猛砸了一下,手一摸,滿臉是血。 顧不上細想,他沖向碉堡,用刺刀在下面刨了個坑,把八顆手榴彈和一個炸藥包碼在一起,一個側滾的同時,拉掉了手榴彈的拉環…… 那一夜,張富清接連炸掉兩座碉堡,他的一塊頭皮被子彈掀起。另外兩名突擊隊員下落不明,突擊連“一夜換了八個連長”…… 真實的回憶太過慘烈,老人從不看關于戰爭的影視劇。偶爾提及,他只零碎說起:“多數時候沒得鞋穿,把帽子翻過來盛著干糧吃”“打仗不分晝夜,睡覺都沒有時間”“淚水血水在身上結塊,虱子大把地往下掉”…… 很多人問:為什么要當突擊隊員? 張富清淡淡一笑:“我入黨時宣過誓,為黨為人民我可以犧牲一切。” 輕描淡寫的一句,卻有驚心動魄的力量。 入伍后僅4個月,張富清因接連執行突擊任務作戰勇猛,獲得全連各黨小組一致推薦,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一個小小的長工,是黨和國家培養了我啊!”時隔多年,張富清的感念發自肺腑,眼角淚濕。 出生在陜西漢中一個貧農家庭,張富清很小就飽嘗艱辛。父親和大哥過早去世,母親拉扯著兄弟姊妹4個孩子,家中僅有張富清的二哥是壯勞力。為了減輕家中負擔,張富清十五六歲就當了長工。 誰料,國民黨將二哥抓了壯丁,張富清用自己換回二哥,被關在鄉聯保處近兩年,飽受欺凌。后被編入國民黨部隊,身體瘦弱的他被指派做飯、喂馬、洗衣、打掃等雜役,稍有不慎就會遭到皮帶抽打。 這樣的生活苦不堪言,直到有一天,西北野戰軍把國民黨部隊“包了餃子”,張富清隨著四散的人群遇到了人民解放軍。 “我早已受夠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我在老家時就聽地下工作者講,共產黨領導的是窮苦老百姓的軍隊。”張富清沒有選擇回家,而是主動要求加入了人民解放軍。 信仰的種子,從此埋進了他的心中。 在團結友愛的集體中,一個曾經任人欺凌的青年第一次強烈感受到平等的對待和溫暖的情誼。 歷經一次次血與火的考驗,張富清徹底脫胎換骨,為誰打仗、為什么打仗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愈發清晰。 “從立功記錄看,老英雄九死一生,為什么不想讓人知道?”負責來鳳縣退役軍人信息采集的聶海波對張富清的戰功欽佩不已,更對老人多年來的“低調”十分不解。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戰的戰士,有幾多(多少)都不在了,比起他們來,我有什么資格拿出立功證件去擺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勞啊,我有什么資格拿出來,在人民面前擺啊……”面對追問,這位飽經世事的老人哽咽了。 每一次,他提起戰友就情難自已,任老伴兒幫他抹去涌出的淚水:“他們一個一個倒下去了……常常想起他們,忘不了啊……” 親如父兄,卻陰陽永隔。在張富清心中,這種傷痛綿延了太久。那是戰友對戰友的思念,更是英雄對英雄的緬懷。 他把這份情寄托在那些軍功章上。每到清明時節,張富清都要把箱子里面的布包取出,一個人打開、捧著,端詳半天。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珍藏的寶貝是個啥。 “我沒有向任何人說過,黨給我那么多榮譽,這輩子已經很滿足了。”如今,面對媒體的請求,老人才舍得把那些軍功章拿出來。 多年來,他只是小心翼翼地,把1954年“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頒發的一個搪瓷缸,擺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這只補了又補、不能再用的缸子上,一面是天安門、和平鴿,一面寫著:贈給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衛祖國、保衛和平。 總會有人問:你為什么不怕死? “有了堅定的信念,就不怕死……我情愿犧牲,為全國的勞苦人民、為建立新中國犧牲,光榮,死也值得。” 任憑歲月磨蝕,樸實純粹的初心,滾燙依舊。 她哪里想到,離家千里去尋他,一走就是大半生。在來鳳這片毫無親緣的窮鄉僻壤,印刻下一個好干部為民奉獻的情懷 1954年冬,陜西漢中洋縣馬暢鎮雙廟村,19歲的婦女干部孫玉蘭接到部隊來信:張富清同志即將從軍委在湖北武昌舉辦的防空部隊文化速成中學畢業,分配工作,等她前去完婚。 同村的孫玉蘭此前只在張富清回鄉探親時見過他一次。滿腔熱血的女共青團員,對這位大她11歲的解放軍戰士一見鐘情。 少小離家,張富清多年在外征戰。 1949年9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張富清隨王震率領的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先頭部隊深入新疆腹地,一邊繼續剿滅土匪特務,一邊修筑營房、屯墾開荒。 1953年初,全軍抽調優秀指戰員抗美援朝,張富清又一次主動請纓,從新疆向北京開拔。 待到整裝待發,朝鮮戰場傳來準備簽訂停戰協議的消息。張富清又被部隊送進防空部隊文化速成中學。 相隔兩地,他求知若渴,她盼他歸來。張富清同孫玉蘭簡單的書信往來,讓兩顆同樣追求進步的心靠得更近。 “我看中他思想純潔,為人正派。”部隊來信后,孫玉蘭向身為農會主席的父親袒露心聲。 臨近農歷新年,孫玉蘭掏出攢了多年的壓歲錢,扯了新布做了襖,背上幾個饃就上路了。 搭上貨車,翻過秦嶺,再坐火車。從未出過遠門的她暈得嘔了一路,嘔出了血,見到心上人的時候,腿腫了,手腫了,臉也腫了。 彼時,一個嶄新的國家百廢待興,各行各業需要大量建設人才。組織上對連職軍官張富清說:湖北省恩施地區條件艱苦,急需干部支援。 拿出地圖一看,那是湖北西部邊陲,張富清有過一時猶豫。他心里惦記著部隊,又想離家近些,可是,面對組織的召喚,他好像又回到軍令如山的戰場。 “國家把我培養出來,我這樣想著自己的事情,對得起黨和人民嗎?”“那么多戰友犧牲了,要是他們活著,一定會好好建設我們的新中國。” 張富清做了選擇:“作為黨鍛煉培養的一名干部,我應該堅決聽黨的話,不能和黨講價錢,黨叫我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哪里艱苦,我就應該到哪里去。” 孫玉蘭原以為,兩人在武漢逛一陣子,就要回陜西老家。誰知他說:組織上讓我去恩施,你同我去吧。 這一去,便是一輩子。 從武昌乘汽車,上輪船,到了巴東,再坐貨車……一路顛簸,到恩施報到后,張富清又一次響應號召,再連續坐車,到了更加偏遠的來鳳。 這是恩施最落后的山區。當一對風塵仆仆的新人打開宿舍房門,發現屋里竟連床板都沒有。 所有家當就是兩人手頭的幾件行李——軍校時用過的一只皮箱、一床鋪蓋,半路上買的一個臉盆,還有那只人民代表團慰問的搪瓷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