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報(bào)道猶如號(hào)角,喚起工農(nóng)千百萬(wàn);她文如彈藥,筆如刀槍?zhuān)鷦?dòng)記錄蘇區(qū)風(fēng)云,成為黨史專(zhuān)家研究蘇區(qū)歷史的珍貴資料。 這是怎樣一段波瀾壯闊的傳奇? 走進(jìn)江西瑞金葉坪布展一新的紅色中華通訊社舊址,當(dāng)年的《紅色中華》報(bào)刊發(fā)的一篇篇報(bào)道、一張張圖片,再現(xiàn)了中央蘇區(qū)那段血與火的崢嶸歲月,傳遞出一股至今依然奔騰不息的精神力量。 理想烙印在鉛字中 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央蘇區(qū)從事新聞工作,有多不容易? “我也害過(guò)坐板瘡、爛腿癥,寫(xiě)稿子、走路,都非常吃力。每天屁股流出的膿、血,粘貼在褲子上,很是疼痛。”曾任紅中社編委的任質(zhì)斌在回憶文章中介紹,由于人少事多,只好趴在床上改稿子或編寫(xiě)稿子。后來(lái)他實(shí)在支持不住了,只好寫(xiě)信向軍委衛(wèi)生部的同志要了藥物注射,才逐漸痊愈。 患上坐板瘡、爛腿癥的一個(gè)重要原因是細(xì)菌感染,那時(shí)的蘇區(qū)衛(wèi)生條件差,藥物緊缺,痢疾、瘧疾和疥瘡肆虐。紅中社的同志們相繼染上瘧疾。 1931年至1932年,中央蘇區(qū)曾集中暴發(fā)傳染病,涉及范圍很廣。在1932年11月21日《紅色中華》刊登的《江西省蘇報(bào)告》中詳細(xì)介紹了蘇區(qū)各地的疫情,如寧都縣數(shù)月患痢疾達(dá)1300余人,興國(guó)縣6月至7月間發(fā)生瘟疫死亡40余人……處在當(dāng)時(shí)戰(zhàn)亂環(huán)境下,蘇區(qū)的干部群眾不僅要和敵軍艱難作戰(zhàn),還要與疾病戰(zhàn)斗。 紅色中華通訊社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初創(chuàng)時(shí)期只有幾個(gè)人、幾張桌子,和《紅色中華》報(bào)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舊址內(nèi)有一座微雕模型,油畫(huà)背景加上9位姿態(tài)各異的微雕人物,還原了紅中社編輯部的場(chǎng)景。 當(dāng)年,紅中社編輯部最多時(shí)也只有10來(lái)個(gè)人,他們常常夜以繼日地工作,很少休息,除采訪(fǎng)、寫(xiě)稿、譯電外,還兼刻蠟紙和校對(duì),常常面臨人手捉襟見(jiàn)肘的局面。 “每星期六下午,從瑞金騎馬去葉坪,在縣城東北,相距約10里……發(fā)病的時(shí)候,也得去葉坪,因?yàn)椴蝗ゾ蜎](méi)有別的人去編了。”這是紅中社早期負(fù)責(zé)人李一氓的回憶,他平時(shí)在中央政府大廳做編寫(xiě)工作。 隨著國(guó)民黨軍隊(duì)對(duì)中央蘇區(qū)的封鎖和“圍剿”日甚,中央蘇區(qū)的食鹽、布匹、日用百貨都陷入緊缺狀態(tài)……要得到這些如今看來(lái)稀松平常的東西,在那時(shí)卻成了奢望。 紅中社工作人員在每人每天僅有半斤糙米的情況下,依然主動(dòng)節(jié)約糧食和伙食,每天僅吃?xún)刹碗s糧。他們用自己的雙手開(kāi)荒種菜,還將自己的被毯、衣服甚至微薄的津貼,毫不猶豫地捐獻(xiàn)出來(lái),送給前方浴血奮戰(zhàn)的紅軍戰(zhàn)士。 雖然《紅色中華》報(bào)辦報(bào)條件簡(jiǎn)陋,影響卻很大,發(fā)行數(shù)量一度超過(guò)國(guó)統(tǒng)區(qū)的《大公報(bào)》。
《紅色中華》報(bào)創(chuàng)辦百期版面。 在《紅色中華》報(bào)百期紀(jì)念時(shí),當(dāng)時(shí)的領(lǐng)導(dǎo)同志特別提出:《紅色中華》報(bào)向困難作頑強(qiáng)斗爭(zhēng)的精神,值得全蘇區(qū)的黨政工作同志學(xué)習(xí)! 是什么樣的信念,讓他們?cè)谌币律偈车娜兆永铮试溉淌芾ьD的生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歷史細(xì)處不忍卒讀,其中多是苦難與犧牲。 紅中社舊址陳列著一張被燒毀的《紅色中華》報(bào)紙殘頁(yè),常常有很多游客駐足。這是紅軍長(zhǎng)征出發(fā)后,瞿秋白等人在蘇區(qū)出版的最后一期《紅色中華》報(bào),給敵人制造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沒(méi)有轉(zhuǎn)移的假象。最后瞿秋白被捕犧牲,書(shū)寫(xiě)了中國(guó)新聞史上悲壯的一頁(yè)。 他們既是新聞人,更是革命者。他們的理想烙印在《紅色中華》報(bào)的鉛字當(dāng)中——“建立獨(dú)立自由領(lǐng)土完整的蘇維埃新中國(guó),才是民族解放唯一的出路。” 讓群眾都能看懂 我們的新聞需要什么樣的文風(fēng)? 《紅色中華》報(bào)的新聞寫(xiě)作堅(jiān)持通俗化方針,要求做到蘇區(qū)每一位群眾都能看懂。 翻開(kāi)報(bào)紙,許多短小精悍的稿件表達(dá)通俗生動(dòng),卻飽含真情實(shí)感,散發(fā)著質(zhì)樸清新的魅力。 在《紅色中華》報(bào)的編輯看來(lái),可以這樣寫(xiě)通訊:“只要你用質(zhì)樸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聞事實(shí)有條理地寫(xiě)下去,那就保你寫(xiě)得括括(呱呱)叫。” 就像通訊員成紫玉在《紅色中華》報(bào)上發(fā)表的這篇體育報(bào)道:“昨(二十二)日演習(xí)閱兵畢,午后一時(shí)許有紅大,特校,軍委無(wú)線(xiàn)電聯(lián)合球隊(duì)與國(guó)家保衛(wèi)局籃球隊(duì)大戰(zhàn)于閱兵場(chǎng),聯(lián)合隊(duì)出場(chǎng)的勇健兒,都是那一班素負(fù)能手的老將……這場(chǎng)籃球戰(zhàn)真所謂‘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在球場(chǎng)里身飛足舞似馬奔騰,那傳球的妙術(shù),直使圍場(chǎng)的觀(guān)眾,不絕喝彩。” 這篇報(bào)道生動(dòng)活潑,畫(huà)面感十足,把當(dāng)時(shí)運(yùn)動(dòng)場(chǎng)上熱鬧而又充滿(mǎn)激情的場(chǎng)景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 即便是記錄“反圍剿”戰(zhàn)斗這類(lèi)題材的新聞,報(bào)道也在字里行間融入生動(dòng)的元素。 有一篇報(bào)道這樣寫(xiě)道:“黃陂紅軍勢(shì)甚活躍,國(guó)府已令鄂省李鳴鐘、皖省邱盛宜、豫省張鈁三省圍攻云。”乍看之下,危機(jī)重重,但文尾卻又加上了一句旁白,“又來(lái)送槍支子彈”,盡顯面對(duì)強(qiáng)敵時(shí)的無(wú)畏,透出豪邁之氣。 為了增強(qiáng)宣傳效果,提高工農(nóng)群眾的藝術(shù)興趣,《紅色中華》報(bào)的副刊《赤焰》應(yīng)運(yùn)而生。 “不是一小顆火星,不是一點(diǎn)子曙光,這是漫山遍野,勢(shì)如燎原,到處都是的赤焰……”1933年4月23日,《紅色中華》報(bào)這首題為《到處是赤焰——紀(jì)念今年的“五一”》的長(zhǎng)詩(shī)激情澎湃。 隨著副刊的開(kāi)設(shè),《紅色中華》報(bào)的稿件體裁、文風(fēng)變得更加豐富多樣,蘇區(qū)群眾能閱讀到各式各樣的話(huà)劇、詩(shī)歌、小說(shuō)等。 《紅色中華》報(bào)的副刊上,還發(fā)表了《送郎參軍》《紅軍打勝仗》等小調(diào)歌詞,歌詞通俗,即便沒(méi)有譜也可照民歌典譜填詞,好聽(tīng)好唱,群眾熟悉,很快能流傳。 “全蘇人民的喉舌” 今年是中央紅軍長(zhǎng)征出發(fā)90周年。于都中央紅軍長(zhǎng)征出發(fā)紀(jì)念館里,展出了一份1934年9月8日《紅色中華》報(bào)刊發(fā)的《募集廿萬(wàn)雙草鞋慰勞紅軍》的報(bào)道,號(hào)召群眾在10月10日前捐贈(zèng)20萬(wàn)雙草鞋。 不到1個(gè)月,募集草鞋的任務(wù)完成。 紅軍,到底有什么“魔力”讓群眾如此擁護(hù)? 歷史的答案,能在《紅色中華》報(bào)上找到。 1934年1月31日,《紅色中華》報(bào)(第二次全蘇大會(huì)特刊)第5期發(fā)表了毛澤東同志關(guān)于中央委員會(huì)報(bào)告的結(jié)論的講話(huà),答案直觀(guān)明了——在他看來(lái),解決群眾的鹽問(wèn)題,米問(wèn)題,房子問(wèn)題,衣問(wèn)題,甚至生小孩子的問(wèn)題,解決群眾一切的問(wèn)題,如果這樣做,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hù)蘇維埃,把蘇維埃當(dāng)作他們的生命。 作為新生的人民政權(quán)的“耳目”“喉舌”,《紅色中華》報(bào)宛如一部生動(dòng)的史書(shū),記錄下蘇區(qū)軍民戰(zhàn)斗生活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她的許多報(bào)道沾泥土、帶露珠,充滿(mǎn)了來(lái)自一線(xiàn)的內(nèi)容。蘇區(qū)的讀者親切地贊譽(yù)她是“我們蘇維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現(xiàn)”“全蘇人民的喉舌”。 例如,報(bào)紙刊發(fā)的《武陽(yáng)區(qū)印象記——春耕運(yùn)動(dòng)的實(shí)際材料》,是一篇走基層的典型稿件,其中寫(xiě)道:“在武陽(yáng)區(qū),我們看到麥子長(zhǎng)在新開(kāi)墾的荒土上……獲得了土地的農(nóng)夫農(nóng)婦,牽著牛兒,肩著耕具,一隊(duì)隊(duì)地走到田垅里去。” 鉛字里有魚(yú)水深情。通過(guò)1934年7月21日的《紅色中華》報(bào),我們得以了解正是在蘇區(qū)干部和群眾攜手努力下,中央蘇區(qū)渡過(guò)困難時(shí)期:“我們這里,雖然處在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的環(huán)境中,雖然今年天氣亢旱,但是因?yàn)樘K維埃政府領(lǐng)導(dǎo)革命戰(zhàn)爭(zhēng)保護(hù)蘇區(qū),因?yàn)樘K維埃政府提倡和指導(dǎo)了春耕運(yùn)動(dòng),開(kāi)墾了荒田,興發(fā)了水利,解決了人力牛力……今年的收成是好過(guò)了去年。” 除了紅軍幫助群眾春耕秋收、興修水利等生產(chǎn)勞動(dòng)的新聞,《紅色中華》報(bào)還報(bào)道了文化、教育等領(lǐng)域和群眾密切相關(guān)的消息。 當(dāng)年,“送戲下鄉(xiāng)”在中央蘇區(qū)是“常規(guī)操作”。 1934年4月至5月,《紅色中華》報(bào)連載了李伯釗撰寫(xiě)的《蘇維埃劇團(tuán)春耕巡回表演紀(jì)事》,記述了中央蘇維埃劇團(tuán)下鄉(xiāng)巡回演出受到熱烈歡迎的場(chǎng)景: “在逢市公演那天,田野外的小道上,一隊(duì)一隊(duì)的婦女們,有的穿了較新的衣服,有的穿了大花鞋,小女孩打著鮮紅的辮子,有的抱著孩子,年老的扶著拐杖,喧喧嚷嚷:‘喂!大家去看中央來(lái)的文明大戲,蠻好看咯!’……” 每逢群眾較集中的趕圩的日子,蘇區(qū)的劇團(tuán)常常前去演出,以密切同群眾的關(guān)系,而對(duì)《紅色中華》報(bào)來(lái)說(shuō),為人民而呼是她與生俱來(lái)的使命。 《紅色中華》報(bào)創(chuàng)辦百期時(shí),張聞天刊文說(shuō),《紅色中華》報(bào)的誕生是在第一次蘇維埃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之后,她是蘇維埃政權(quán)下千百萬(wàn)工農(nóng)勞苦群眾的喉舌,她是同群眾的生活不能分離的。 幾乎每期都刊載國(guó)際新聞 當(dāng)年的蘇區(qū)干部群眾,雖身處偏僻山村,卻目光如炬,見(jiàn)識(shí)不凡。他們?cè)谂鉀Q自己生存問(wèn)題的同時(shí),放眼全國(guó)、環(huán)顧世界。 那時(shí),“美國(guó)財(cái)政虧損”“南美玻利維亞與巴拉圭激戰(zhàn)”都是他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就連北極小鎮(zhèn)伊加卡的極晝極夜也為人所知。 為了讓蘇區(qū)干部和群眾能了解國(guó)際時(shí)事,《紅色中華》報(bào)上開(kāi)設(shè)了“國(guó)際風(fēng)云”“世界零訊”“國(guó)際時(shí)事”等欄目,幾乎每期都刊載國(guó)際新聞。
《紅色中華》報(bào)發(fā)刊詞。 他們?yōu)楹稳绱酥匾晣?guó)際報(bào)道?《紅色中華》報(bào)《發(fā)刊詞》一語(yǔ)道破緣由:“使工農(nóng)勞苦群眾,懂得國(guó)際國(guó)內(nèi)的政治形勢(shì)。” 蘇聯(lián)是《紅色中華》報(bào)關(guān)注最多的國(guó)家,內(nèi)容涵蓋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生活等各個(gè)領(lǐng)域。彼時(shí),蘇聯(lián)成立不過(guò)十余年,《紅色中華》報(bào)滿(mǎn)懷著熱情與好奇,注視著這個(gè)親切又遙遠(yuǎn)國(guó)度的一舉一動(dòng)。 “在北西伯利亞,有一座位于北極圈內(nèi)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那里生活著三十多個(gè)民族,夏季河流開(kāi)凍之時(shí),小輪船行駛十四五天就能到達(dá),冬季則是漫漫長(zhǎng)夜,溫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dāng)z氏度。” 1933年1月,《紅色中華》報(bào)一則消息,向讀者介紹了伊加卡的情況。那時(shí),北極對(duì)蘇區(qū)群眾來(lái)說(shuō),已不再那么神秘,“北極”一詞在《紅色中華》報(bào)上共出現(xiàn)15次。 傳遞國(guó)際消息,無(wú)線(xiàn)電報(bào)務(wù)人員功不可沒(méi)。1933年5月,原在中革軍委總部電臺(tái)第六分隊(duì)工作的岳夏,受命建立“紅色中華新聞臺(tái)”。新聞臺(tái)建立后,能夠直接抄收中央社的國(guó)際消息和外國(guó)通訊社的電訊。《紅色中華》報(bào)較多轉(zhuǎn)載塔斯社、路透社等國(guó)外通訊社稿件,內(nèi)容多關(guān)乎莫斯科、倫敦、華盛頓這三大信息中心。 《紅色中華》報(bào)尤其關(guān)注鄰國(guó)日本的動(dòng)態(tài),多報(bào)道日軍的侵華動(dòng)態(tài)及宣傳國(guó)內(nèi)的抗日運(yùn)動(dòng)。即使在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局勢(shì)如“黑云壓城城欲摧”之時(shí),她依然牽掛著“日本帝國(guó)主義鐵蹄下的華北滿(mǎn)洲”。 在紅中社舊址內(nèi)抬頭仰望,一方藍(lán)天鑲滿(mǎn)這棟客家農(nóng)舍的天井,這是革命火炬曾經(jīng)熊熊燃燒過(guò)的天空,湛藍(lán)而高遠(yuǎn),也讓我們對(duì)“革命理想高于天”有了更加直觀(guān)、真切的感受。 《紅色中華》報(bào)的歷史恰似一幅波瀾壯闊的畫(huà)卷,理想和信仰是她的底色,每一筆每一劃,都書(shū)寫(xiě)著理想與情懷。 回望歲月的長(zhǎng)河,那些在病痛中依然堅(jiān)持采寫(xiě)新聞的身影,那些充滿(mǎn)溫度和力量的文字,那些朝氣蓬勃的年輕面孔,永遠(yuǎn)值得懷念和銘記。(記者李興文 賴(lài)星) |
檢察機(jī)關(guān)依法對(duì)戴道晉涉嫌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案提起公訴
2024-11-08
中國(guó)海警艦艇編隊(duì)11月8日在我釣魚(yú)島領(lǐng)海巡航
2024-11-08
攔河建壩、私設(shè)排污口 貴州銅仁生態(tài)破壞問(wèn)題突出
2024-11-08
今年秋招,你遇到“AI面試官”了嗎?
2024-11-08
快遞業(yè)務(wù)量井噴,智能快遞柜是否“失寵”?
2024-11-08
旺季提前到來(lái),快遞小哥迎戰(zhàn)最長(zhǎng)“雙11”
2024-11-08
普惠金融保量穩(wěn)價(jià)優(yōu)結(jié)構(gòu)
2024-11-08
2025年軍隊(duì)文職人員公開(kāi)招考工作全面展開(kāi)
2024-11-08
- 日榜
- |
- 周榜
- |
- 月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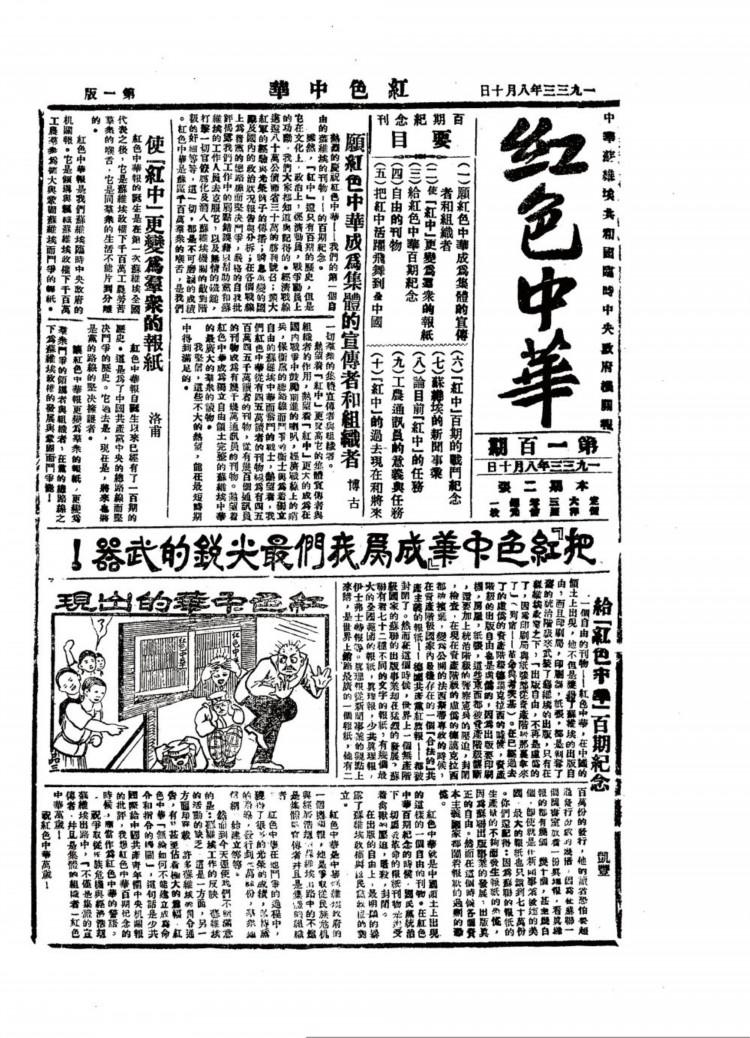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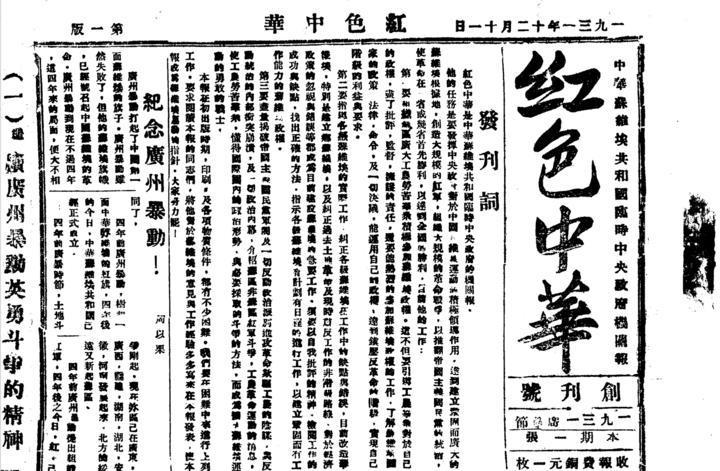
ad19de1b-027c-49a4-96eb-700a5239b8ca.jpg)
05d80a6b-ef02-4c60-92ba-6d1c25244cf6.jpg)
63628c5c-2cd7-44da-8677-409e9e3e65cc.jpg)